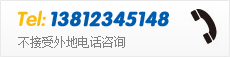杨周律师,江苏连众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连云港市优秀律师,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具有法律本科、会计专科学历,熟悉经济,精通法律,擅长公司法律事务。从业以来,能够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恪尽职守,坚持诚信为本、专业取胜的执业理念,杨周律师先后为连云港电视台、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峰矿业(连云港)有限公司、连云港盐业公司、连云港天地经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数十…[详细介绍]
杨周律师,江苏连众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连云港市优秀律师,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具有法律本科、会计专科学历,熟悉经济,精通法律,擅长公司法律事务。从业以来,能够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恪尽职守,坚持诚信为本、专业取胜的执业理念,杨周律师先后为连云港电视台、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峰矿业(连云港)有限公司、连云港盐业公司、连云港天地经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数十…[详细介绍]
谁来给年轻律师一碗饭吃?
下午从“星巴克”回来已经快七点钟了,想着冰箱里没什么库存了,就去超市买些吃的回来。拎一堆东西出来,看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蹲在马路边,用衣服挡住脸,面前的地面上写着“我好饿,请好心人给我五元钱,买盒饭吃。”因为这种场景在深圳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我眼睛瞥了一下就径行走了过去,刚刚走过去几步,想着那张痛苦的脸我不禁停住了脚步,好好看看了一下蹲着的男孩,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如果不是被迫无奈,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可能如此屈尊如此丢人现眼的。我翻了下口袋,还有十几元零钱就全掏出来过去塞到他手里,说了声:快去吃饭吧。他接收了我的钱,脸都不敢正面看我一下。
在深圳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很多人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来了就能挣到钱,结果来了后才知道找工作有多难,钱有多难挣。由于准备不足再加上没有老乡或朋友帮助,就只能落得在大街上行乞的尴尬境地。
想想年轻律师的生存还不是一样,前不久我在北京期间,深圳的一名年轻律师打电话给我,说他快顶不住了,刚刚在办理转所手续,可是接受他的律师事务所在办理手续时又额外要他交纳几千元保证金,否则不予办理调档手续,为此他一下子晕了。因为办理转所已经几个月没有收入了,老家还有一个弟弟上大学需要他扶持,家里父母还要其供养,为此他已经背负了好几万元债务了。如果再交纳保证金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感觉几乎快崩溃了。我一时无语,只有告诉他接受挑战,先与所里协商不行再考虑更换一家律师事务所,等我从北京回来再帮助他一起想办法。其实在他办理转所前我就为他推荐了几家提成制的所,但是他却没有去,也许患得患失,自己业务量不够,又担心提成制会吃亏是主要原因(回深圳后经电话联系,他已经与律师事务所协商同意先为其办理转所手续)。
现在年轻律师生存之艰难的盖子至今也没有完全被揭开,也不被社会所共知,社会上普遍地认为做了律师一定能赚大钱,甚至还总被张冠李戴地被戴上“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帽子。
其实律师一旦成为律师后就成为了“三无人员”,无工资保障、无社会保障、无业务保障。而且从律师成长的一般规律来看,必然要经历“五年之痒”的过程,就是说律师成长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五年左右的业务技能、经验和资源的积累期,这个“五年之痒”就是横亘在年轻律师面前的一座“雪山”,很多年轻的律师就在这座雪山前“倒”下了,能爬过去的已经是寥寥无几。中国律师业自2000年以来一直徘徊在十一万余人的水平上,表明这个行业已经容不得后来人了。
一个容不得后来者的行业怎么会有前景和发展?面对这一困惑,显然律师行业本身已经无力解决,设想一下,如果律师业中的有二十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与刚刚取得执业照的律师都挤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平等竞争,年轻律师怎么可能会有竞争力,怎么可能容得下后来者?
上述现状造成的原因到底是律师事务所的体制问题,还是行业制度问题、还是社会制度问题,这到了不得不好好反思的时候了。多年来笔者一直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当然作为律师业内人士有责任也有义务好好反思自己,首先是从律师事务所体制、行业制度来寻找的答案,为此笔者写了大量的文章,通过专业化、团队化、公司化、国际化等方式解决律师事务所的可持续性发展。但是如果社会的总供给不足,也就是说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蛋糕没有增大的情况下,不管律师业或律师事务所采用何种体制或机制,仅仅是同一块蛋糕的不同分割,分来分去结果总还是大同小异。
为什么我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对法律服务的总需求相对不足呢?究其原因:
一、传统观念的制约
从传统社会中走来的人,至今仍然顽固地以为,律师就是打官司代名词,大多数中国人都格守着不打官司不找律师积习。以至大多数人都是在事后找找律师,而不是事先与事中找律师,需求上的缺陷导致律师服务上的缺陷,虽然近几年来,这些状况有所改善,但也仅仅限于公司业务、公司的上市与兼并等,而这类业务总是不是有限,总是集中在有限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手上,不可能成为普通律师的日常业务,不是普遍的业务,这几类业务的出现不可能能对律师现状产生根本的改变。大部分的人依然是在原有的观念下看律师、请律师。
二、旧的计划经济时期体制的约束
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法院包办一切,许多本由社会中介机构、律师办理事务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由政府包办代替了。一个人从生下来开始到去世一切的法律手续几乎都可以不依赖律师的帮助来完成。政府对此也习以为常,老百姓对这种状况也习以为常了,彼此都习惯使用和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免费资源。至今在小政府、大社会时代背景下,老百姓遇到什么问题,仍然习惯于一层一级地找各级政府上访告状,而不是找律师提供帮助,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由于政府资源是免费资源,而律师服务是有偿服务,所以导致社会排斥律师、政府排斥律师、百姓排斥律师的局面,而百姓遇到问题愤愤不平到处告状,顽固地躺在政府的免费资源襁褓中,求保护、求保障、求保全,求公平、求公正、求正义,如此,政府是顶着石臼唱戏——吃力不讨好,不处理又不行,处理也是力不从心,而老百姓因无法充分享受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包办式服务而倍感失落感和抱怨。政府与百姓在公共资源的争夺战中打得难解难分,结果是把律师凉在一边饿得半死。
三、新兴的事务产生与发展没有为律师留一杯羹
目前现在我们社会上有几大怪:
1、 人生大事婚丧嫁娶可以不找律师。
2、房地产买卖可以不找律师。
3、注册、注销公司可以不找律师。
4、重要的交易、买卖(比如车、船、土地使用权等)甚至打官司都可以不找律师。
而上述事务中都要经过复杂的法律手续才能完成,其中要么放任自流,造成政府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出生登记,结婚、离婚登记、死亡登记或户籍注销等,老百姓为办理完这些事务往往要往返、反复多少次,才能完全享受到政府的服务;要么就由普通的中介机构把持,比如公司注册、房地产买卖、车船买卖等等,由于面广量大,政府事实上无法起到实质性的监管的作用,使这些重要的社会事务事实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由于中介公司的恶性的低价竞争,导致律师根本无法介入到这些社会事务中,帮助政府或当事人规范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完善法律手续,并导致产生了大量的纠纷和矛盾,进而导致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也使律师作为一个行业被社会冷落。
四、国家在制度上没有为律师的执业提供必要的保障
从现有的律师业务来看,除了上市、兼并、改制等业务国家规定必须要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诉讼业务除了律师其它人不能提供有偿服务,其它越来越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务由国家规定必须由律师参与的事务,几乎是屈指难数。
显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果政府不能充分利用律师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作用,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管理难度,同时也因监管不力而导致放任自流状态,公司注册业务与房地产买卖业务表现是最典型的,因为在政府与相对人之间缺乏中间的监管环节,即使出了问题没有人承担责任。
假如由律师代替政府行使审查或规范的职能,一方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律师在参与过程中必然自动获得了一种对社会事务的监管责任,政府可以通过对律师的管理来达到对社会事务的管理。
比如:
1、国家规定出生登记、死亡登记等必须由律师参与并出具相应的证明,显然政府会省事、当事人也省心,同时也能化解许多的因出生与死亡产生的财产纠纷与继承纠纷。
2、公司注册与注销必须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对投资人或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的法律意见书或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依法清理的出具相应的证明或意见。就会大大减轻工商行政机关的审查工作量,同时对其中弄虚作假法乱纪的行为,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要求律师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管理律师或达到对公司的注册注销过程进行全面监管,如此一方面大大地节约了政府资源,同时也有序地规范公司注册注销的秩序。
3、在房地产买卖过程中,必须要由买方的律师对房地产合同出具合法有关键所在法律意见书,如此将更有利于保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开发商在房地产买卖过程中真正起到约束、限制、规范作用,保障买卖双方真正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下进行公平的交易。
4、对重要、重大的生产资料或财产,法律强制性规定必须由律师参与并出具相应的法律意见书,方可办理产权登记或变更,如此即能增加交易的品质和质量,省去大量的政府资源同时也避免大量的纠纷产生。
综上所述,法律服务的市场总需求不足,不仅仅是市场问题而是制度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律师业发展的瓶颈与困境,必须从制度上予以创新,赋予律师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
如此社会的总需求增加了,整个律师业才会有大的发展,年轻律师也因法律服务的总需求增加而获得更多的服务机会,才可能有业务保障,所以谁来给年轻律师一碗饭吃?答案应该是政府。政府也只有政府才能给年轻律师以保障,让年轻律师起码有一碗饭吃。
华律网邱旭瑜律师(天上的虫子)
2006年7月5日12时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