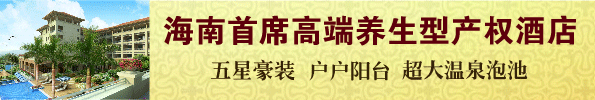杨周律师,江苏连众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连云港市优秀律师,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具有法律本科、会计专科学历,熟悉经济,精通法律,擅长公司法律事务。从业以来,能够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恪尽职守,坚持诚信为本、专业取胜的执业理念,杨周律师先后为连云港电视台、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峰矿业(连云港)有限公司、连云港盐业公司、连云港天地经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数十…[详细介绍]
杨周律师,江苏连众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连云港市优秀律师,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具有法律本科、会计专科学历,熟悉经济,精通法律,擅长公司法律事务。从业以来,能够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恪尽职守,坚持诚信为本、专业取胜的执业理念,杨周律师先后为连云港电视台、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峰矿业(连云港)有限公司、连云港盐业公司、连云港天地经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数十…[详细介绍]
张思之:人权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
信息来源:杨周律师网 发布日期:2014-05-10 06:09:33
阅读次数:5960
 13607989 位注册用户,目前在线 51917 人
13607989 位注册用户,目前在线 51917 人 [转帖]张思之:人权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
347 次点击
0 个回复
也许是因为他几十年来为无数素不相识的人的命运奔波,却从来避免对自己的宣传,包括著名记者卢跃刚曾多次表示希望为他写一本传记,都被他婉言拒绝;也许是因为他所代理的案件经常被视为“敏感”而不宜公开审理,使他的工作没有更多的进入公众的视野,在很多年轻人脑海里“张思之”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在同行中,这位见证并参与了整个共和国法制发展历程的老人,被誉为“中国法律界的良知”。江平先生评价张老“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张老的辩词和梦想已经超越了个人经历的意义,成为我们社会法制信念的标竿,正如当代汉语研究所对他的颁奖词里所说的:“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老的工作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职业的内涵,他在为自由和人的尊严辩护、为历史公正辩护、为苦难的中国人民辩护。
免于恐惧的权利
郭:在我印象中,您的青年时代,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动荡时期,当时热血青年脑海里想得都是革命、救国,您是如何会想到专攻法律呢?
张:在我解放前我最想学的其实是外交,一心想“外交救国”,同学中可能向往“科学救国”的多一些,因为小时候我非常难受的思考我们国家为什幺这样积弱,为什幺总受人欺负,当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看到那些丧权辱国的协议,非常愤怒。将中国之所以搞不好归罪于外交的失败,认为缺少好的外交家,谈笑风生,折冲尊俎,来维护中国的利益,我以为一个国家的尊严靠的是外交。现在想来那时候实在是太天真幼稚了。
当时培养外交官的学校只有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大学,那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校,里面的学生一毕业就是县级干部,多数当了“党棍”,当时一些热血青年都是不甘当“党棍”的,我只好另选专业,由于外交和外文、法律接近,有人介绍我说北京的朝阳法学院不错,就学了法律。解放以后我就当了法官,再后来就当了律师,也算命中注定。
郭:您被人称作“中国人权律师”,对这个称呼您如何看待?
张:维护人权其实是律师的职责,众所周知法律保障的重心正是人权,理算当然,律师执业的重点也必定是人权,所以律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天然的人权维护者。人权需要维护说明我们还存在问题,有些环节,有些方面没有落到实处,得不到100分甚至有些方面还不及格。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的优劣,外国人说三道四,本国人可以不认帐。但也不能由本国的上层人士、白领阶层、手握重权的肉食者说了算,得让身居下层的芸芸众生认可才算数。外出讨生活的农民工,不要说与劳动部长比就是和工会主席比也会有不同的体验。如果硬说我们享受了多少人权,我这个普通律师,还真没这种感受。因此我要求自己通过自己的工作致力于维护人权。遗憾的是,我做得实在不够好,非常有愧。
郭:那么政府在维护人权方面因该扮演什幺角色?
张:现在我们也提倡“权为民所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用在维护人权上。我向你这样年轻的时候,曾经以为一个国家只要有好的外交或者强大的国防就有面子,后来才明白一个道理,其实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国家能把人权维护好,国家就有了荣誉,在国际上才有面子。我们过去各朝各代,总把爱国家和爱政权甚至爱政党爱领袖混为一谈是讲不通的,一个政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幺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他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你说是不是?
郭:您对人权问题有什幺具体的意见?
张:历史上仁人志士对人权有很多很好的见解,我只能谈一点个人的想法。比如说,我最不赞成把“生存权”突出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人权讲的是做人的权利,理所当然指的是人生存于世之后的那部分与生俱来的权利,也就是人一样的生活,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有人认为十几亿人有饭吃,就证明人权状况良好,那么奴隶社会的奴隶,有了饭吃,得了“生存”,是否就有了“人权”?用不着再求“解放”了?而且我们有过几年之内饿死几千万人的记录,我们把它归咎与“自然灾害”。我常想,如果他们有了足够的“人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那么这种惨剧是否可以避免。
仿佛还有一种说法,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改善人权得慢慢来才行。这是“人权上授”观的典型反映,问题在于人权不是一种赐予,而是与生俱来、自然享有的权利,不容剥夺,谁违反了就应该承担责任,不然还要立宪干吗?
郭:您所理解的人权的具体内涵是什幺?
张:我的认识也都是常识性的,来自于学者们的专着,不过你这一问,让我不禁想起罗斯福谈到的“四大自由”,罗斯福的自由观我并不觉得有多高妙,不过他的“四大自由”里面的一条“免于恐惧的自由”说的太到位了。罗斯福真是了解社情,尤其是下情。
郭:远古的人恐惧来源于自然灾害和野兽。您觉得当前我们的恐惧来自于何方,是否是一种体制性的压迫?
张:我想拿事实说话,你看我一个年近八旬的老翁,有没有恐惧?我可以如实告诉你,我有,经常有,在执业中时时会有。往事就不提了,说个近例,我承接了上海郑恩宠律师“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案”,郑的妇人来北京同我探讨上诉的辩护事宜,她刚下火车,我们正通电话就被掐断,跟着不明身份的几个大汉,将她强行拽回上海,这无疑是有关方面对我施加威慑,我应二审法官之约到上海交换意见,除法院外,只去了看守所,但始终两辆警车尾随,每辆车上都有几位“便衣”,最后一直送我到虹桥机场,看我离去。面对此景,我尽管未患“神经衰弱”,也不免想到何时自己也会陪郑君入狱,这就是一种“恐惧”。恐惧不免,谈何自由,我一个近八旬的老头,身为律师,自己尚不免恐惧,还奢谈维护人权,真是天大的讽刺,让我无言以对。
对人权我感受很深的还有一层就是“表达权”。我觉得我们尤其需要一种可以公开表达自己对公共生活的看法的生活,一种在强势的政府面前也能不卑不亢的生活。我们目前在实际操作中,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宪法还有很大差距。你说话一不小心就可能犯了反革命罪,这样的社会不是靠公民的认同,而是靠暴力为后盾的威严来统治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公民不能免于恐惧的国家,只会培养寻租和投机,不会有真正的安居乐业。我们有一些斗争年代的思维方式,是不适应当前政治文明需要的。
即使在“花瓶”里也要插一枝带刺的玫瑰
郭:目前很多学者都在探讨司法独立的问题,您这幺多年来实践思考的体会是什幺?
张:其实不要太高估我,我早先也是政府的“驯顺工具”,“一颗螺丝钉”,党让我干什幺,我就干什幺,当时我作江青的辩护律师,也不是自己的选择,完全是组织的安排,可能是他们觉得江青这个人太厉害,要找一个能对付她的人(笑)。直到文革以后一系列发生在我们民族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教训逼着我反省,让我认识到这一切的荒诞,我才觉得大师陈寅恪提倡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多幺可贵,这真是做人的准则、做事的圭臬。
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司法独立是难于做到的,法院能不参加就个案组织的专案组提前介入?法官能不理会某个上级的批条或者指示?又有哪个法院能够违抗政法委的指示?组织安排其实也就是长官意识,在目前的民主集中制下,一个长官的拍板是很难抵抗,他可能听取了一些人的汇报下了一个结论,这就是上级党委组织的决定和意见,这个决定也许是科学的也许是不科学的。我并不认为当前所有的法官都是素质低下的,他可能也对法律怀有信念,但他没有能力抵抗来自行政的干预,因为他的一切身份乃至待遇福利都是这个行政系统和政权结构中的一环,除非他有勇气抛弃这一切,而他抛弃以后又很快有听话的人来接替他的位置。对于他自己也从内心不认同的行政干预,他也许也会顶顶牛,但最后他必需服从政治,服从组织安排,说得好听点叫做服从大局,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是这个官僚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其次才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很多情况下法律成为了权力的仆人。
前不久办一个关于律师被捕的案子,法官跟我谈话,我直截了当问他“你能不能排除行政独立办案?”他回答也很实在:“我只能说,我跟你谈话此时此刻没有受到干扰。”那么过了“此时此刻”呢?他没说,也不方便说。但我从心里还是希望法官能一个个案子排除干扰秉公办理,总会有水到渠成之日,当然我也寄希望于有更多高素质的优秀法官。
郭:当前的法制环境下,律师经常处在尴尬的位置,我见过一些律师有钱的官司才接,在法官和雇主之间拉皮条,而且无奈的说:社会现实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另一方面社会上不公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律师才算老几啊?要管也管不过来,您如何看这样的态度?
张:我们国家是有人把现在的中国律师称作花瓶,我想不是全无道理。但就算是在花瓶里,你也有权利决定是插上一只含露带刺的玫瑰还是一把狗尾巴草。越是恶劣的执法环境下,律师越是要自重。我一直认为只有大案子才接,只有名人的案子才接,只有效益好的案子才接是低级趣味的具体表现。真正的律师眼里案子没有大小的区别,更没有名人和老百姓的区别。
诚然天下不平事太多,律师不能包打天下,但问题在于只要大众有需求,我们就无权推诿,不然要律师干嘛?有一次我代理一个案子,姑且把他们称作有关部门吧,来了两个干部,找我谈话,跟我作工作说这个案子影响面太广,你就不要管了。我反问他,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当事人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律师,你该怎幺办,你接还是不接?他们楞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后在再也没来找过我。
我想勤勤勉勉和包打天下不是一回事,有时候我也确实忙不过来,只有让其它律师代理,而我接案子没有什幺标准,如果我硬要找标准,只能说问问良心,是不是不管不行,我想人同此心,情同此理,总有你实在坐不住的时候。
至于律师和法官的关系这是一篇大文章,从两面相互影响的密切来看,我只想说一句“别相互腐蚀”,如果不能及时清楚我们队伍中的“败类”,无疑会败了我们的队伍!
作一个律师该作的事情
郭:律师常常受到来自政府和公众两方面的压力,前一段时间为刘涌案辩护的律师受到很多的攻击,认为他和法律的敌人站在一边,你怎幺看这个情况?
张:任何人都有被辩护的权力,哪怕是大奸大恶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我支持有律师站出来为刘涌辩护,收律师费也无可厚非,至于价钱是否合理我不了解情况,不敢妄言。